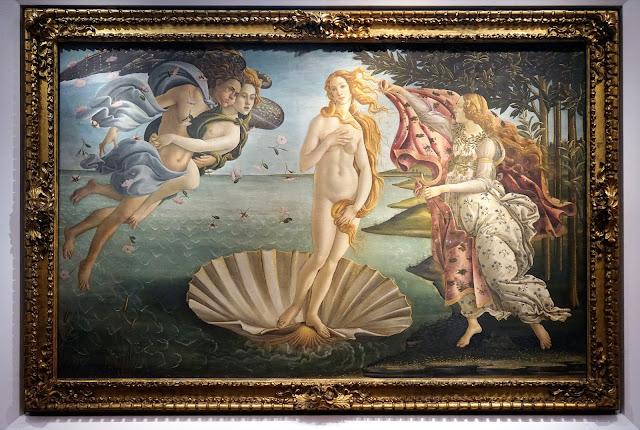|
如果你對這位巴洛可大師不太了解,這篇網誌也許是一個起點: 羅馬: 聖王路易教堂(San Luigi dei Francesi):浪跡天涯的巴洛可大師:卡拉瓦喬(Caravaggio)的故事。
 | |
|
這展覽還有一個副題,叫做”畫家的摯友與敵人”。原來同時借到許多與卡拉瓦喬同時期,在羅馬發展的畫家作品,這讓展覽的內容更為豐富。
由於沒有事先買票,所以就要現場排隊了,別看只有幾十人排隊,因為展場實在不大,所以在寒冷的巴黎早晨,排了約一個小時才得以入場。
Jacquemart-Andre Museum 原先是一個巴黎銀行家富二代的豪宅,主人Edouard André與她的妻子Nélie Jacquemart用了十幾年的時間四處蒐集藝術品,並帶回巴黎,安置在他們美麗的家中。
Jacquemart在年輕的時候便是一位有名的女畫家,她在三十歲的時候,曾經幫André畫了一幅畫像,誰知道十年之後,兩人再次相遇,André決定與四十歲的Jacquemart廝守終身。但這個決定遭到André家族的極力反對,Jacquemart 為了證明自己不是貪圖財產,便簽署婚前協議書放棄財產的擁有權。她們的婚姻由1881年持續到1894年,André就過世了。但是他在遺囑中還是將遺產全部留給了Jacquemart,家族不服氣,告上法院,但法官將龐大的遺產判給了Jacquemart。Jacquemart持續著藝術品的收集工作。1912年她以70歲的年紀過世。過世之後將所有藝術品與這棟豪宅捐給了法蘭西藝術學院。這也是她先生André的最大心願。
當然這博物館也還是蠻漂亮的。不過還是來看畫吧!!!
我們順著展覽室欣賞這些畫。我先介紹卡拉瓦喬的畫,再談一下其他人的搭配畫作。
第一間展覽室
 |
| 2018/10攝於巴黎Jacquemart-Andre美術館: 《朱麗絲的復仇》 |
《朱麗絲、女僕與亞述大將的頭(Judith and Her Maidservant with the Head of Holofernes), 1611》
這幅畫是Orazio Gentileschi (1563–1639)的作品。
 |
| 2018/10攝於巴黎Jacquemart-Andre美術館: 《朱麗絲、女僕與亞述大將的頭》 |
Giuseppe Cesari (1568-1640)的《大衛與巨人(David avec la lete de Goliath) 》
 |
| 2018/10攝於巴黎Jacquemart-Andre美術館: 《大衛與巨人》 |
下一幅是Giuseppe Cesari (1568-1640)的《大衛與巨人(David avec la lete de Goliath) 》
 |
| 《大衛與巨人(David avec la lete de Goliath) 》:2018/10攝於巴黎Jacquemart-Andre美術館 |
接下來又是一幅《燭光中的朱麗絲與亞述大將何樂弗尼的頭(Judith with the Head of Holofernes), 1610-1618》
 |
| 《燭光中的朱麗絲與亞述大將何樂弗尼的頭》:2018/10攝於巴黎Jacquemart-Andre美術館 |
這裡展出的依然是朱麗絲色誘亞述大將的故事,這裡面的燭光效果絕對來自卡拉瓦喬的風格。而俏寡婦朱麗絲以清純美少女的造型呈現也算是一絕了。但是看了幾遍之後,赫然由她眼神中看出了一些果決與凶狠。
Carlo 與卡拉瓦喬有甚麼關係麼? 原來當卡拉瓦喬在1606年承包了羅馬聖瑪麗亞德拉斯卡拉教堂(Santa Maria della Scala)的工程,畫成了《聖母瑪利亞之死(Death of the Virgin), 1606》這幅畫。
 |
| 《聖母瑪利亞之死(Death of the Virgin), 1606》2018/3 攝於巴黎羅浮宮 |
第二間展覽室是以靜物的寫生作為主題,卡拉瓦喬的早期作品中常常出現水果、樂器之類的靜物。這應該是與他羅馬生涯的第一個工作有關,他在Giuseppe Cesari 工作室的工作,有許多都是描繪靜物,這造就他對於靜物獨特的觀察力。
第一幅當然是要看 Caravage 這幅《彈琵琶的女孩 (Suonatore di Liuto, 1595-96)》。
 |
| 《彈琵琶的女孩 (Suonatore di Liuto, 1595-96)》: 2018/10攝於巴黎Jacquemart-Andre美術館 |
 這畫借展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冬宮博物館(Ermitage Museum, San Pietroburgo),能在巴黎看到這幅畫也算是極大的確幸。這幅畫還有兩個類似的版本,一幅在大都會博物館,另一幅在英國。不過東宮版的內容多了一個花瓶,也更為豐富一些,算是最完整的版本。
這畫借展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的冬宮博物館(Ermitage Museum, San Pietroburgo),能在巴黎看到這幅畫也算是極大的確幸。這幅畫還有兩個類似的版本,一幅在大都會博物館,另一幅在英國。不過東宮版的內容多了一個花瓶,也更為豐富一些,算是最完整的版本。這些畫都是為了紅衣主教弗朗西斯科的特殊喜好而繪製的,也都賣給了他。而他的子孫一次一次的將畫賣了出來。這幅畫最先流落到巴黎,俄國沙皇在拍賣會中買下了這幅畫。
但是藝術史的討論集中在這幅畫的那不男不女的主角是誰? 目前的定論是他一定是男的。但是學者分為兩派,一派認為那是他的男朋友Mario Minniti,Mario在那時候幾乎是卡拉瓦喬敝人的主角。
另一派認為他是一位叫做Pedro Montoya的教堂歌手,那時候為了為了保持童音,教堂歌手常常會去勢以免變聲,Pedro 就具備這樣的身份,而且他也是紅衣主教弗朗西斯科身邊常常出現的人物。
而冬宮博物館這幅畫中的每個物品,包含花瓶中的花朵、琵琶琴或是樂譜都極度寫實。這幅畫最厲害的部分是花瓶的瓶子,因為他把一個透明的玻璃瓶、水與倒影都畫出來,真的非常厲害。
這裡的第一幅畫是 La Douleur d’Aminte (1605-1610),現為Marco Voena的私人典藏,但是卻長期在羅浮宮展出。Marco Voena是誰我也不知道? 但牆上這麼寫,我就照抄。
 |
| 《Aminte 的痛苦(La Douleur d’Aminte, 1605-1610)》:2018/10攝於巴黎Jacquemart-Andre美術館 |
第二幅是《水果與靜物(Nature Morte a la corbeille de Fruits, 1614 ~ 1620)》,現藏於 Fondation Palatine, Vaduz (Liechtenstein Museum)
 |
| 《水果與靜物(Nature Morte a la corbeille de Fruits, 1614 ~ 1620)》:2018/10攝於巴黎Jacquemart-Andre美術館 |
 |
| 《聖塞西莉亞和兩個音樂天使(Sainte Cécile et deux anges musiciens, 1615) 》: 2018/10攝於巴黎Jacquemart-Andre美術館 |
另一幅畫是 《Sainte Cécile (1620) 》。
 |
| 《Sainte Cécile (1620) 》: 2018/10攝於巴黎Jacquemart-Andre美術館 |
來到第三間展覽室。這間是一些裸體的小孩子為主題的畫,我不是古板的人,但依然覺得很奇怪十七世紀的人們可以接受這樣的作品。
第一幅自然是卡拉瓦喬的 1602的作品法文叫做《施洗者聖約翰與公羊 Le Jeune Saint Jean-Baptiste au belier, 1602》, 或義大利文《施洗者聖約翰(San Giovanni Battista, 1602)》。
 |
| 《施洗者聖約翰(San Giovanni Battista, 1602)》:2018/10攝於巴黎Jacquemart-Andre美術館 |
畫的主角是聖約翰,由於聖約翰小時候曾經是沙漠中的牧羊人,又具備了先知身份,畫中親密的抱著一隻羊是可以理解的,但是為什麼不穿衣服呢?
因此這幅畫雖然是宗教主題,但繪製目的是純作為私人欣賞之用,我想也的確難登大雅之堂。歷經幾次轉手之後,最後收集到了羅馬山丘博物館中,但在1902年突然離奇失蹤,1950又突然在羅馬市長辦公室中被找到,於是歸還給山丘博物館。難道當時的羅馬市長又有特殊喜好,…,好吧!!! 就不八卦下去了。
Annibal Carrache - L’Adoration des Bergers
 |
| Annibal Carrache - L’Adoration des Bergers - 1597-1598: 2018/10攝於巴黎Jacquemart-Andre美術館 |
不幸的是當法拉瓦喬成名之後,巴洛克風格主導了主流藝術的走向,這讓卡拉奇的晚期事業非常吃鱉,而在48歲即抑鬱而終。這裡展出的畫作來自於奧爾良美術博物館(Musée des beaux-arts d'Orléans)
這裡展出的畫作是Giovanni Baglione在1601年承包羅馬耶穌會總部Gesù教堂的祭壇畫。
 |
| 《耶穌的復活(La Résurrection du Christ, 1601 – 1603)》2018/10攝於巴黎Jacquemart-Andre美術館 (借展於巴黎羅浮宮) |
 |
| 德國柏林的大畫廊(Gemäldegalerie, Berlin)展出的兩幅畫 |
Baglione所承包的這幅教堂作品於1603年復活節完成,當拿到教堂準備交貨的時候,教堂委員會已經被抹黑的風評所影響,決定不予驗收,同時用另外一位作家作品取代了Baglione的作品。
Baglione氣炸了便告到法院,卡拉瓦喬公開宣稱,他雖然不認識Baglione,但是這作品畫的極為愚蠢,任何一位畫家一眼都可以看出來一毛不值。
從此Giovanni Baglione的畫遭到大師的公開認證之後,便真的一敗塗地,幾乎失去所有生意。Giovanni Baglione 畫畫的生意失敗之後,便開始寫書來混口飯吃。他學習前輩瓦薩里,寫了兩本藝術史的書,詳細的記錄了文藝復興晚期約兩百位畫家的生平事蹟。現代的藝術史學家,如果想研究後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,必然要看他的書。他也是我教堂故事的前驅者,因為他的第一本著作便是《羅馬的九個教堂(Le nove chiese di Roma 1639》。
Giovanni Baglione 總共寫了寫了兩百多位畫家的傳記,包含卡拉瓦喬,想必不會有太好的評語。